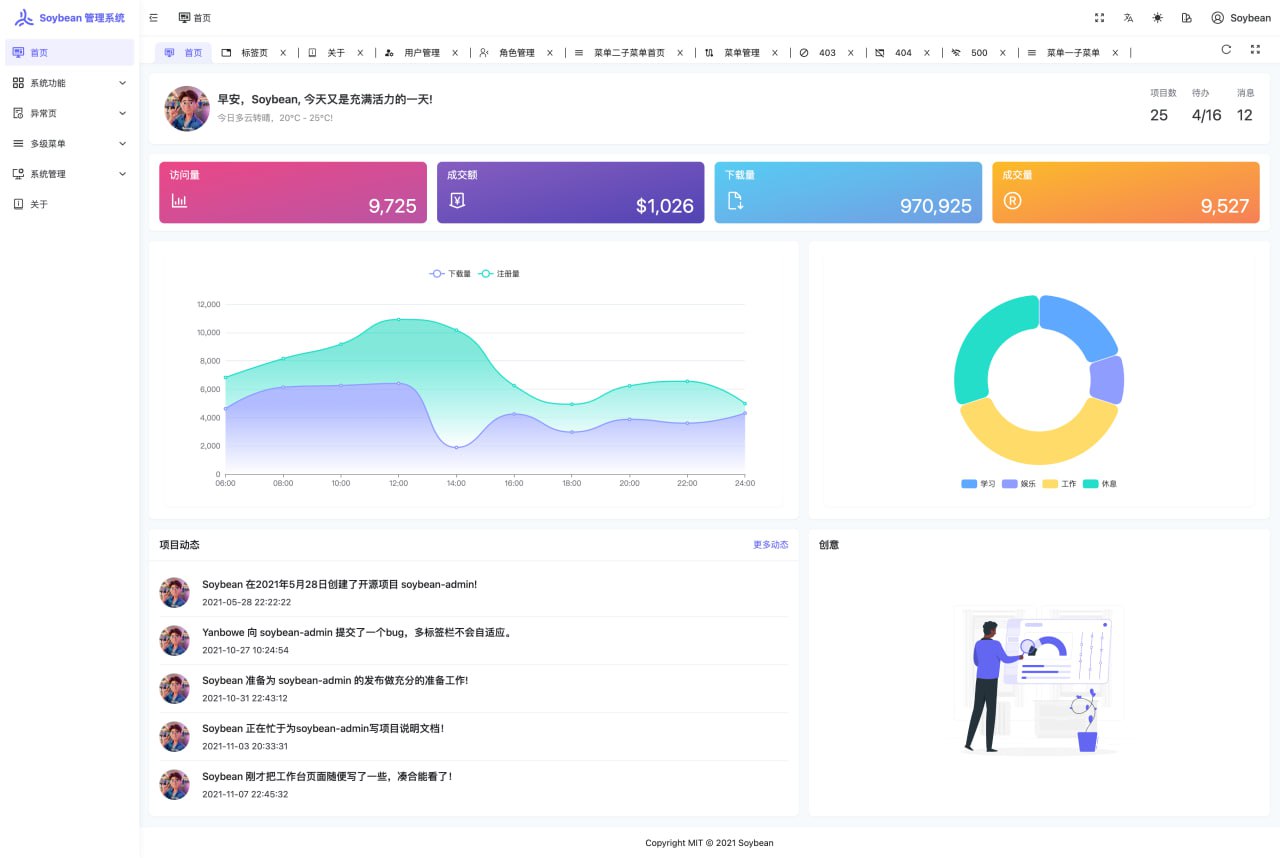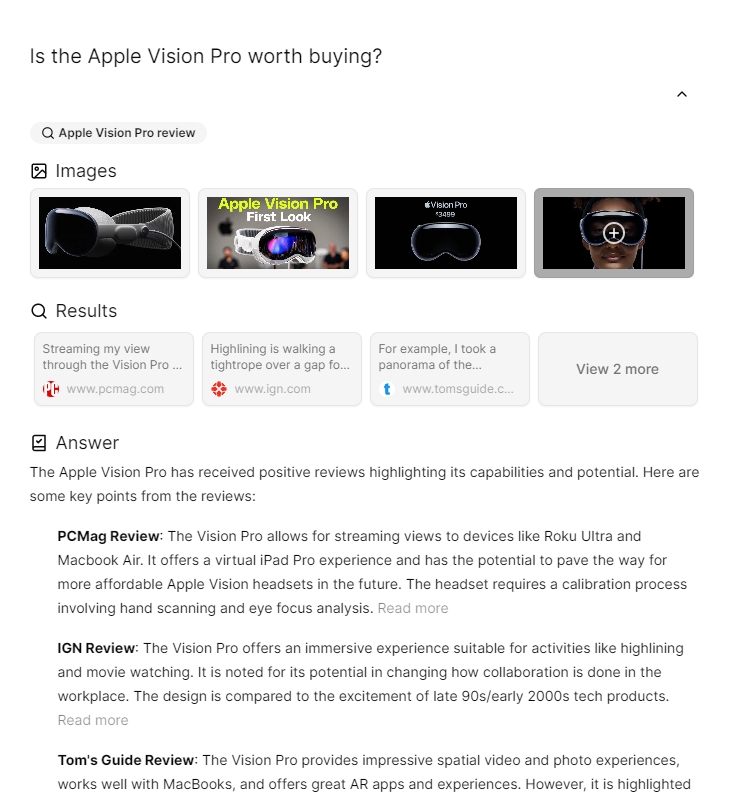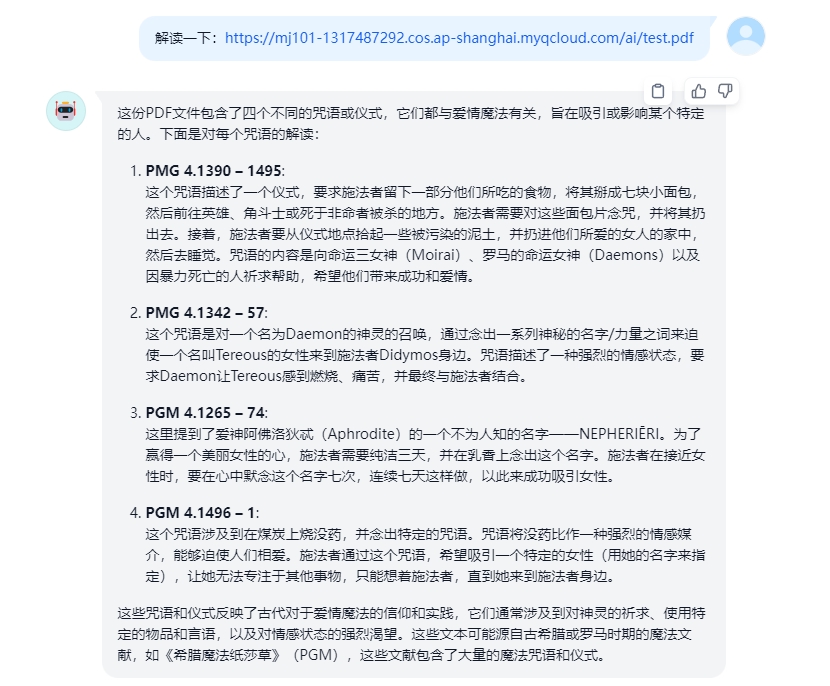“厌童潮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?
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和父母去北京,那时我不到七岁,还没有上学。第一次坐火车硬卧,兴奋得不得了,我从来没有见过上中下三层铺的床,于是一遍遍顺着栏杆爬上去,再发明各种姿势跳下来。火车上的方便面真香啊,几乎人手一盒,每个人都给盒里倒上开水,再花漫长的三分钟等面泡开。我站在车厢里说,要是能天天吃方便面该有多幸福啊。周围听到的人都端着面碗笑了。
说实话,我对那次旅行目的地的印象十分淡薄,爬长城、游故宫、吃北京烤鸭,我都不太记得了,只能从留下的照片中找到这些事情发生过的痕迹。可时过境迁,我唯独记得那节小小的车厢,人们擦身而过,透过窗外的风景判断下一站将要停靠在哪里。狭窄的走廊上永远弥漫着泡面味道,推着小车的售货员前来兜售纪念品,有人会买,有人只看看,又放回去。许多人走过会摸我的头,问我一些再寻常不过的问题,你几岁啦?多高啦?上学了吗?要跟爸爸妈妈去哪里玩呀?火车上短短的两天一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,却占据我这段旅行中的最美好的记忆。
事情究竟是从何时起了变化,已经不大能说得清了。或许是从飞机上的幼童父母体贴地给周围人预备歉意小礼物开始,也或许是无数人点赞列车上的“关音菩萨”开始,总之,儿童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,而携带儿童的父母似乎也带有某种“原罪”。
诚然,为人父母确实应担负起教导孩子遵守公共场合相关规定的责任,但如果孩子还小,或者孩子尚不能完全服从父母的管束,对他们的厌烦乃至歧视就可以理直气壮吗?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“我终于当了一次关音菩萨”为傲?为什么越来越多带孩子的父母在踏上高铁和飞机时,没有旅行开始的兴奋,而是心怀忐忑与恐惧?
车上的许多人都挂着一张菜色的脸,有的张嘴仰头,在座位上昏昏欲睡;有的在狭窄的小桌板上架起电脑,勾着脖子艰难打字;更多的人是在玩手机,刷短视频,看网文,打游戏。不知为何,即便是在娱乐和放松,人们依旧显得如此疲惫。高铁与飞机都比从前的绿皮火车快得多,人们坐在高铁飞机上,仿佛也被传导了某种加速度。不管是工作还是旅行,那种“美好风景都在路上”的心态一去不返。
人们着急,很着急,因为旅行完了就要工作,工作完了还有工作,耐心像沙漏一般,在日复一日的徒劳与奔忙中被一点点耗空。因此没有欲望、也没有能力去共情那些带孩子的父母,遑论那些精力旺盛的孩子呢。
南大法学院的周安平老师曾说过:
社会是由不同人所组成,因此也就需要互相容忍,这是社会延续下去的基本条件。每一个人都为别人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承担一定的容忍义务,才能保证这个社会不破裂。
不难想象,一个人的容忍底线取决于他(她)个人的修养、所受的教育、家庭的环境以及他(她)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,当一个成年人变得敏感易怒,渐渐丧失对儿童的耐心,即意味着他(她)的容忍底线正在崩坏,相应地,也意味着他(她)恐怕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生活。
我们确实应该做出一些行动来帮助吵闹的孩子与孩子的父母,但与此同时,也应该给那些厌童者多一点关注,他们可能正在“生病”(或许他们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),而当“厌童”成为潮流,成为群体性的症候,可能就是社会的病与时代的病了。
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。
版权声明:本站内容为原创和部分整理自网络,如有侵权务必联系我们删除,保障您的权益,本站所有软件资料仅供学习研究使用,不可进行商业用途和违法活动,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